作者|駱斯航
簡介|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系政治理論方向在讀博士生
興趣|馬克思主義、政治情感、政治記憶、文化大革命
編輯|黃靜佳
前言
「虛偽」也許是政治舞台上最常見的道德指控之一。一旦政治家的行為被發現與他們口頭堅持的信條不一致,他就有可能失去公信力,從而喪失公眾的支持。揭露對手的不真實因此成為了一種常見的政治武器。「真實」和「虛偽」這對矛盾關係,足以刻畫虛偽在政治中的作用和危害嗎?從朱迪斯·施克萊(Judith N. Shklar)和讓-保羅·薩特對虛偽的不同刻畫里,我們也許能一窺虛偽在政治中的用途與危害。
正文
「建制派自由派一邊支持積極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一邊利用自己的社會背景把自家小孩送到最精英的私立學校里,太虛偽了……」在隨著特朗普的競選活動而興起的對自由主義建制派精英的批評里,這樣的指控比比皆是。古今中外,「虛偽」可能是政敵的互相攻擊中最常見的道德指控。批評「偽君子」的人往往會把偽君子在不同場合的類似問題中抱有的雙重標準或者在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原則不一致作為證據,以此來揭露偽君子的虛偽。但遭到攻擊的往往不只是偽君子的人格,同時還有偽君子口頭上所堅持的政治信條。如果一種政治信仰連口口聲聲追隨它的信徒都無法堅持,那這種信仰本身還剩下多少說服力呢?抱著這樣的想法,我們似乎自然而然地認為虛偽是政治中的嚴重惡行。
虛偽是政治中的首惡嗎?當代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家朱迪斯·施克萊明確反對這一論點。施克萊為虛偽做了現實主義的辯護,她認為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下,虛偽是政治難以根除的衍生品。比起舉起道德大旗攻擊虛偽,我們還有更恰當的方式來對待虛偽。施克萊對虛偽的辯護讓我們理解虛偽在政治中的潤滑作用,但她的辯護同時也要求我們進一步去思考滋長虛偽的結構性因素。從薩特的《存在與虛無》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不同於施克萊著重論述的虛偽的不真實:自欺(bad faith,又譯壞信仰)。薩特的自欺概念告訴我們,滋生虛偽的不僅僅是政治土壤,還有現代人維繫其生活的社會土壤。薩特所描述的這種新型的虛偽,在政治中不僅不能起到施克萊所期待的潤滑作用,對政治本身還有著獨特的負面影響。
 |
| 虛偽攻擊的不只是政客偽君子的人格,同時還有偽君子口頭上所堅持的政治信條 |
虛偽的用途
只有少數幾種惡能支持自由主義民主政制,虛偽就是其中之一。【1】在《平常的惡》的結尾,施克萊告誡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在多元社會的政治里,要有能力超越對人的精神內在、人的究極動機的追問,忍受虛偽,將注意力放在更嚴重的政治惡行中去。施克萊的這個建議當然不是憑空而來。虛偽總體上而言是一種欺騙,但它是一種特殊的欺騙:它使得偽君子獲得了與其自身不相稱的道德評價。施克萊並非認為虛偽是一種值得贊頌的個人美德,也清楚地意識到「虛偽是一種強制的形式……強迫他人對某人作出比他實際應得的更高的評價,這是完全不公平的,而令人如此憤怒的正是這種不公平。」【2】但在她看來,如果我們對人的真誠抱有一種不切實際的嚴格要求,那這種要求本身可能就是虛偽的——我們自己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這種真誠呢?因此過於嚴苛的道德標準,反而可能變成滋長虛偽的土壤。在政治中,對真誠的過高期待也可能帶來負面的結果。施克萊認為,既然自由民主政治的核心機制是說服與妥協,那麼所有的政治參與者就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運用修辭的藝術來進行偽裝,這本身就說明在自由民主政治里,虛偽是無法被根除的。如果政治家之間的互相批評,或者公眾對政治家的批評僅僅局限在「某個政治家到底有多虛偽」這個層面上,首當其衝的問題就是公共政治討論的基礎會被摧毀,公共政治討論會變成一場永不落幕的「相互揭露的遊戲」,在這個過程中「遊戲玩家的騙術則普遍獲得了提升。每一方都在試圖摧毀對手的信用,政治活動於是就變成了矯飾和揭露的無聊遊戲。」【3】這樣的遊戲使政治本身無法獲得任何建樹,因為我們的注意力都被消耗在了漫長反復的人身攻擊之中。
但這樣的遊戲還有一個更大的風險。施克萊認為,在更深的心理基礎的層面上,一種充滿恐懼的文化才是使「虛偽和反虛偽都以各種表現茁壯成長」的根本原因。【4】結合她在《恐懼的自由主義》中的立場來看,施克萊認為在政治中,恐懼往往來自於與政治權力如影隨形的暴力與殘酷——而暴力與殘酷,正是施克萊認為的政治中的首惡。換句話說,虛偽的存在往往意味著政治暴力和政治殘酷在某處蠢蠢欲動,虛偽的存在也讓施行政治暴力變得更加容易,但這不意味著我們就應該把虛偽視為和暴力一樣的首惡。如果我們不加分辨地覺得虛偽的善行和殘酷的暴力是一樣壞的,那我們在對虛偽過於嚴苛的同時,就是在對暴力過於寬容,而這在日常的政治辯論中並不罕見。譬如,如果我們僅僅沈浸在指責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虛偽的道德指控中,那有可能就會忽視這種虛偽——哪怕僅僅是一種虛偽——也許就強過了赤裸裸的屠殺和殘害。這正是施克萊在她的政治理論中堅持要為惡行排序的原因,因為「視虛偽為首惡最終會使我們陷入過分的道德殘忍,太過輕易地使我們面臨厭世的誘惑,並擾亂我們的政治平衡。」【5】
通過對虛偽的討論,施克萊實際上探討了促使虛偽產生的政治土壤,這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首先,暴力與殘酷幾乎總是與政治如影隨形,這要求自由主義政治家自己達成同時也與公眾達成「以殘酷為首惡」的共識;其次,不同群體在政治中的訴求往往迥異,他們彼此之間甚至完全可能真誠的互相敵視;最後,由於前兩個條件的存在,政治家需要說服的藝術,也就需要偽裝。施克萊認為上述政治土壤無法輕易被改變,因此才做出了「虛偽這種個人品德上的惡行可能是政治上的德行」這樣的判斷。但施克萊似乎並沒有意識到,政治不僅僅是自上而下的。它不僅僅是政治家和政治家之間的合作與攻擊,也不僅僅是公眾對政治家的道德監督;政治還包括各種自下而上的公民政治參與。既然政治不只是「廟堂之上」的權力活動,我們在考察虛偽在政治中的作用時就不能只把目光聚焦在政治家身上。如果政治本身的定義過於狹窄,我們就無法充分地理解虛偽在政治中可能表現出來的多種形態。在下文里,我們將探討一種與施克萊的政治家虛偽不同的新型虛偽,那就是薩特筆下的自欺。
 |
| 虛偽並不是政治的首惡 |
新型的虛偽:自欺
施克萊所描述的這種政客式偽君子,我們可以稱之為「經典偽君子」。經典偽君子由三個條件構成。第一,偽君子與受眾之間存在清晰的分界,偽君子是欺騙者,受眾是被欺騙者;第二,偽君子有充分的認知能力,掌握全部信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真實目的與偽裝之間的區別;第三,偽君子的偽裝帶有明確的目的,在政治家的角鬥中,這種目的通常是以種種方式獲取權力位置。這種經典偽君子不一定是徹底的道德犬儒,他們可能保留了一些道德准則,只是認為在政治中有比堅持道德准則更重要的事。如果是這樣,那當經典偽君子的偽裝被拆穿時,他們可能還會多少感到一些良心不安。換句話說,道德質問對於經典偽君子而言,不見得完全沒有作用。
但經典偽君子並不是政治中唯一一種偽君子,施克萊自己多多少少地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借由黑格爾之口,施克萊簡單地討論了一種新型的虛偽。這種新型偽君子和經典偽君子的最大不同,在於他們並不會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虛偽。他們會「把高貴、無利害且無私心的意圖貼到自己的所有行為之上,以此改變自己的良心。他就是自己良心的唯一導師。」【6】換句話說,如果說經典偽君子是有意識地欺騙他人來換取自身不應得的道德地位的人,新型偽君子就是欺騙自己來使自己相信自己有不應得的道德地位的人。要這樣做,新型偽君子就得改變自己的良知。新型偽君子沒有掌握他的真實目的和偽裝之間的區別,他相信自己為自己戴上的所有道德高帽。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新型偽君子甚至是「真誠」的——他相信自己言行一致。這樣,即便我們指責新型偽君子虛偽,拆穿他的偽裝,也無法使他自我反省。
對這種新型虛偽進行了深入骨髓的分析的人是薩特。在薩特看來,經典的虛偽一定存在著偽君子與受眾的二分。偽君子是完全知情人,受眾是完全不知情人,這使得偽君子可以選擇隱瞞真相。新型的虛偽則是一種自欺。在自欺里,偽君子和受眾的二分被取消了,「沒有犬儒主義的說謊,也沒有精心準備騙人的概念。」【7】自欺者既是知情人,又是不知情人。自欺者的心因而處在一種二元活動中:一方面,他努力地想保存自己所掩蓋的東西——若非如此,他大可直接放棄這些東西,不必欺騙自己;另一方面,他又無法完全接受自己所掩蓋的東西,因此他需要不斷地抑制、偽裝這些東西。自欺因而是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通過不斷的自我否定(self-denial),自欺者完成了身份認同。但這種認同不是積極的而是消極的;也就是說,自欺者並不是把自己認同為「我是怎樣的人」,而是認同為「我不是怎樣的人」。
 |
| 自欺里,偽君子和受眾的二分被取消了 |
人為什麼能以這樣的狀態自處呢?薩特舉了這樣一個例子:
設想一位初次赴約的女性,她很清楚與她約會的對象有什麼意圖。她迷戀對方由於愛慕她而表現出來的行為和態度,但出於種種原因又不能或者不打算當即做一個決定。於是她主動無視對方的行為表示的「時間性發展的可能性」,忽略對方所有清晰的、關於未來發展的意圖,把對方的行為圈定在當下的範圍內。比如說,如果對方告訴她「我如此欽慕您」,她會消解這句話所表現出來的情慾,將之理解為一種純粹的恭敬和善意,就好像在描述「桌子是圓的」這樣的事實一樣。但實際上,完全脫離情慾的恭敬和善意又無法滿足她,她需要完全向她個人展示的、獨佔的感情。於是她的心處在一種二元活動之中:她想掩蓋對方的情慾意圖,又試圖保存這份情慾本身。在這樣的情況下,甚至連對方更直接的表示她也可以忽視。當對方握住她的手時,她知道任憑他握住這只手便是贊同了調情,便是參與,而縮回這只手就是打破了這份情慾所依存的曖昧和和諧。關鍵是要盡可能拖延做決定的時間——於是她任憑對方握住她的手,卻在精神上脫離了這個時刻。她無視自己的手,開始高談生活——她完成了身體和心靈的分離。【8】在薩特看來,這位女性就是自欺的現代人的範本。她的核心難題在於她無法面對她的決定權以及她的決定所產生的後果。為了逃避決定的重量,她使用各種方法來維持自欺,一面維繫她在情慾中的需要,一面將自己的需要偽裝成單純的善意。在這個過程中她完成了一個消極的自我認同:「我不是對方情慾的對象。」薩特認為這正是現代人存在性問題的核心癥結:脫離了宗教、家庭、部落等各種前現代關係的現代人不再背著枷鎖步履維艱,他獲得了自主權——自己為自己做決定的自主權。他的身份變成了他所做的決定的主人,也就是說他就是他做的決定本身。但和決定相伴而來的是決定的後果:作為決定的主人,現代人必須為自己的決定產生的後果負責。可現代人唯一沒有做的決定是出生,他沒有決定自己要生存在這樣的世界里。於是現代人發現他「是孤獨的,沒有救助的,」他被遺棄在一個自己「對其完全負有責任的世界」。【9】這份無法逃避的責任的沈重感時刻壓迫著現代人,逼迫走投無路的現代人發展出新的心理防禦機制來維持生存。
於是像那位赴約的女性一樣,「我們在自欺中逃避焦慮,」進而逃避現代人的自由。【10】自欺像一場酣夢,現代人難以醒來,是因為像海野綱彌的名言一樣, 「逃避雖可恥但有用」——即便這種「有用」僅僅是以一種心理慰藉的形式存在。在薩特眼裡,自欺當然不只是一種在政治中才存在的問題。它是一種集中體現了現代人全面的無力感的社會性疾病。在《存在與虛無》中薩特給出的自欺案例也都是生活式的。但依照薩特給出的症狀,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敲這種因無法面對自己而產生的新型虛偽以及與之配套的生活方式,對政治有怎樣的影響。
 |
| 「我們在自欺中逃避焦慮」,進而逃避現代人的自由 |
自欺與政治
新型虛偽和經典虛偽之間的不同會讓我們很快就意識到新型偽君子無法完成施克萊設想的「潤滑政治」的作用。如上所述,施克萊所刻畫的經典偽君子,由於他們能夠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偽裝與真實目的之間的區別,因此如果他們保留了一些良知,沒有變成徹底的道德犬儒,那在良知與偽裝發生強烈的碰撞的時候,公眾或者自己的道德拷問也許對他們的行為還有一定的限製作用。施克萊為虛偽所作的現實主義辯護實際上也或多或少地依賴於這種限制。誠然,作為公眾的我們並不會幼稚地期望政治家像聖人一樣自覺堅持道德操守,我們也很清楚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中道德聖人也許會一事無成,但很多時候我們也許仍希望政治家在被迫做出不道德的決定時,會陷入不安和掙扎。換句話說,對於樸素的偽君子而言,即便我們按照施克萊的建議容忍他們,這樣的容忍往往也建立在一種虛偽是一種面對現實環境的權宜之計(modus vivendi)的基礎上,而不是在道德上為一切虛假的政治行為鬆綁。但薩特所刻畫的自欺的新型偽君子,既不具備執行權宜之計所必須的認知能力,也不具備必須的能動性,這說明基於真誠的道德拷問對自欺者是無效的——因為自欺者真誠地相信自己的謊言,真誠地相信自己為了逃避自由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因此這種虛偽顯然無法完成施克萊所期待的「潤滑政治」的作用。
但既然政治不僅僅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家之間的權力角鬥,我們就不能只從這個角度來理解自欺對政治的影響。對於自下而上的各種公民政治參與而言,自欺又有什麼影響呢?公民政治參與的各種形式,不管是遊行、抗議還是示威,常被看作是有賦權感(empowerment)的政治行動。這是因為在政治信仰的號召下,政治參與者經常在參與過程中感受到集體行動的力量和參與者彼此之間形成的情感連接,從而獲得行動的力量感。如果如薩特所言,自欺的根源是現代人無可依靠的無力感,那麼我們能否認為,政治參與對於解決自欺問題,有某種益處呢?換句話說,如果自欺是一種壞的信仰,那我們能用一種政治上的好信仰(good faith)予以改造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理解薩特眼中「信仰」所預設的心理結構。在薩特看來,所有的「相信」或者「信仰」都蘊含了一層帶有自我否定的不確定性。例如,當一個人說「我相信我是勇敢的」時,他一定同時知道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怯懦的——否則他會說「我是勇敢的」,而不會使用「相信」這個表述。也就是說,所有「相信」的狀態都是同時包含著肯定與否定的矛盾的,或者叫「存在的內在分裂」。【11】好信仰與自欺式的壞信仰之間的區別,在於好的信仰會通過批判性的思索來檢驗自己所堅持的信條,也檢驗自己是否符合這些信條,從而積極地向信仰靠攏,亦即向「肯定」的一端靠攏。自欺則相反:自欺者不會批判性地思考自己堅持的信條。當事實證據出現,證明他的行為和他口頭堅持的信仰不符時,他逃向「否定」的那一端,通過否定事實來維持自欺的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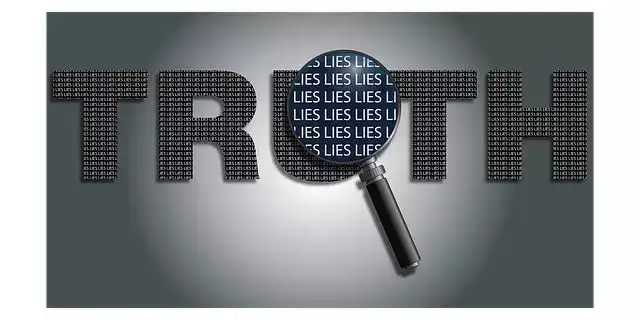 |
| 所有的「相信」或者「信仰」都蘊含了一層帶有自我否定的不確定性 |
回到公民參與的例子中,我們就會發現,給自欺者提供一種政治信仰,使他們參與到政治活動中,未必見得有所助益。政治參與誠然是塑造新的、政治的、共同體式的自我的機會,但它完全也可能只是在給自欺者提供更多自欺的理由。如果政治信仰的信條未能經過參與者的批判性思索,自欺者就不會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和自己的政治主張不一致。即便這種不一致被揭露,自欺者也會逃避現實,對自己的言行不一視若無睹。對於白人女權主義(white feminism)的批評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問題。白人女權主義常被詬病只關注社會頂層的白人女性所遇到的不公正待遇,既忽視有色人種女性(women of color)所面對的來自種族和性別等多方面的多元壓迫,也忽視自己作為白人女性在社會中已經享有的特權地位。假設這一批評屬實,受到這種批評的白人女權主義者未必一定是刻意欺騙的經典偽君子。她們的失明更可能是一種薩特描述的自欺,一種被無法面對自身的特權地位與女權主義信仰之間的落差所激發的逃避。因此她們可以無視自己的特權地位,真誠地相信自己的女權主義主張,也相信自己的行為是在為好的目的服務。也就是說,政治參與也許可以提供一個塑造自我的機會,但這需要自欺的生活模式以某種方式被打破,否則政治行動的道德口號無非是在給自欺者提供更多的素材。
這樣的政治參與不僅僅是對自欺者無益,對政治本身也會帶來傷害。既然自欺的核心是逃避決定的重量,那自欺式的政治參與,實質上就是將自己的政治決定權不加批判地轉交給了政治信仰。缺乏力量感和自我認知的參與者有被煽動者操縱的風險,這一點埃里希·弗洛姆早在《逃避自由》中就提醒過我們,自欺者逃避責任的心理有可能促使他們將自己的能動性轉交給獨裁型政治權威,從而進一步導致極權主義式的政治運動和政治體制的形成。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也試圖說明,在歐洲帝國主義擴張的過程中形成了以集體逃避責任為目的的部落式民族主義(tribal nationalism)。精神上無家可歸的遊民被部落式民族主義所吸引,匯聚在一起,是極權主義動員的重要群眾基礎。
對於期望發動更多參與者的政治運動而言,自欺的政治參與還有一層更深的危害。回到白人女性主義的例子里,白人女性主義受到批評的原因,不僅是它擠壓了有色人種女性的發聲空間,更因為它讓旁觀者或者潛在的參與者認為「女權主義運動無非就是這樣自欺欺人的」。這就傷害了場運動的凝聚力和動員力。而這正是自欺對政治運動,尤其是有良善目的的政治運動最入骨的傷害:作為一種壞信仰,它佔據了所有崇高的道德話語,使得真正的好信仰無處容身。試想,如果一個坐在學院中安享小資產階級生活,對現實中的不平等視若無睹的人也可以被稱為「馬克思主義者」,那我們用什麼話語來形容真正戰鬥在一線,在生產場域里組織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行動者?如果在在社交網絡上時不時點點轉發,轉載一兩篇關於性別平權的文章就可以被稱為女權主義者,那我們用什麼話語來形容為女權事業犧牲個人安穩生活的女權行動者?一旦政治信仰被自欺者搶奪,旁觀者、潛在的參與者,甚至是既有的參與者就都可能對真誠的政治信仰是否存在產生懷疑。如施克萊所言,虛偽最令人憤怒的地方在於它是一種脅迫。但它不止脅迫我們給偽君子戴上不相稱的道德光環。在政治參與中,它更脅迫我們的政治想象力,使我們懷疑真誠一致的政治信仰是不是可能存在。這樣的懷疑如果蔓延開來,後果就是一種對政治的全面不信任,犬儒主義的陰影恐怕就山雨欲來了。
 |
| 政治參與也許可以提供一個塑造自我的機會,但這需要自欺的生活模式以某種方式被打破 |
結語
「虛偽」也許是政治舞台上最古老、最常見的道德指控,但政治中的虛偽也許不止一種。如果說施克萊刻畫的經典的、權術式的虛偽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不是最首要的惡行,甚至有可能對政治本身提供一種潤滑劑作用的話,薩特所刻畫的自欺式的虛偽,對政治有著更深層次也更難以察覺的傷害。
這就是為什麼馬丁·路德·金在《寄自伯明翰監獄的信》里著重提醒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政治參與中有一個重要的步驟是自我淨化(self-purification)。自我淨化意味著所有政治參與者都需要清晰地知道運動的最終目的、達成目的所需要付出的犧牲,以及自己能否付出這樣的犧牲。這樣的自我淨化,不只是發生在某個重大的集體行動之前的;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參與者反復錘鍊自己的認知和良知,甚至需要不同的參與者之間互相錘鍊。這個過程毫不容易。但做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參與者,本身就是一件道德要求嚴格的工作。摒棄自欺式的虛偽,則只是這項工作的準備和起始而已。
作者志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thank Volker Schmitz for the conversations crucial in developing this essay.
注釋
- 朱迪斯·施克萊,《平常的惡》,錢一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252頁。
- 同上,51頁。
- 同上,68頁。
- 同上,51頁。
- 同上,88頁。
- 同上,73-74頁。
- 讓-保羅·薩特,《存在與虛無》,陳宣良等譯,三聯書店,2007年11月,106頁。
- 同上,87-88頁,為縮略轉述。
- 同上,674頁。
- 同上,675頁。
- 同上,106頁。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