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丁
簡介|北京大學哲學系16級本科生
興趣|古希臘羅馬政治哲學、倫理問題、共和主義傳統的近現代發展
編輯|黃靜佳
前言
在《論李維》中,馬基雅維利以羅馬為共和自由的範例,討論了共和國擴張與維持的諸多問題,不僅包括了共和國擴張與維持中諸多技術性的指南,還包括了對羅馬政制安排的獨特刻畫。在當代的討論中,不同流派均重視《論李維》這一核心文本,特別是聚焦於「敗壞」、「自由」【1】等核心概念的討論。馬基雅維利在使用這些概念時未進行明確的定義,而其論述也散見於紛繁複雜的事件分析中,使得較難還原出完整的、貼合馬基雅維利文本的解釋。共和主義的代表學者斯金納和波考克均就這些問題給出了精彩的論述;然而在筆者看來,斯金納和波考克都沒有對於《論李維》I.4中「動亂」這一概念所揭示出的羅馬政制結構予以足夠的重視,這也影響了他們對馬基雅維利的整體解釋,甚至使得其論述難以完全咬合馬基雅維利的文本。在本文中筆者將試圖論證如下內容:(1)斯金納與波考克對馬基雅維利人性、公民德性的理解與概括均不充分;(2)無論是斯金納強調的法律,還是波考克強調的軍事-宗教秩序都沒有全面地揭示出馬基雅維利所理解的、維繫羅馬共和國自由的根本力量:上述內容得以發揮作用仰賴於平民與貴族間的良性互動,以及精英的「處決」為其發揮作用奠定基礎;(3)羅馬共和國的平民走向敗壞、喪失自由,也同時是平民與貴族良性互動的結構遭到破壞的結果。
 |
| 馬基雅維利像 |
一、 問題的提出:斯金納與波考克的人性圖景
波考克在《馬基雅維利時刻》中,以「德行(virtù)」與「命運(fortuna)」的關係展開,討論了羅馬如何在時間的語境中通過德行(virtù)的力量,使得羅馬人的自然本性可以被改造以適合公民身份,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超時間的公民德性(virtue)。在波考克看來,公民宗教與軍事紀律構成了重要的社會化機制:公民宗教使得羅馬人成為適格的軍人,而軍事紀律和公民宗教使得羅馬軍人關注公共善,培養出同公民身份相匹配的公民德性。【2】習俗(costumi)只能扮演第二自然的角色,而公民德性目的在於發展人的「原型」(prima forma);【3】然而同時,公民德性依賴於習俗對人第二自然的塑造,第二自然卻又會在時間中敗壞。【4】故而在波考克的區分中,敗壞被解釋為質料(人民)的第二自然發生變化,導致質料從公民德性的原型中退化,而公民德性自身不會發生變化。【5】波考克將公民德性描述為「理想的實現狀態」,【6】堅持這一立場,則在公民德性得到保持時,公民作為質料已經發展出了良好的形式,可以將公共利益放在自我利益之前,保持政治參與和軍事武裝的自主性。但是根據馬基雅維利文本的刻畫,在公民德性保持時,平民仍然有諸多無法擺脫的劣根性,【7】公民德性的保持與將自身利益放在公共利益之前的傾向同時存在於未敗壞的羅馬人民【8】(特別是平民)身上,甚至羅馬人會做出危害共和的行為。這對波考克的人性解釋構成了嚴重的挑戰。
相較而言,斯金納給出了更加符合馬基雅維利刻畫的解釋。斯金納認為在保持公民德性之時,人民仍然會保持自私的模式與動機,以及自我毀滅的傾向;【9】在法律的強迫之下,人民得以避免自我毀滅的傾向,維持共和國的自由以及公民的自由。【10】綜合斯金納的分析以及馬基雅維利的文本內容,人民(特別是平民)主要存在如下傾向:擁有凶悍的性情卻易於接受奴役(《論李維》,I.16);無法認清自己的利益,且易於被欺騙,難以被明智的建議說服(《論李維》,I.53);易於出於私利行事,只有在必然性之下才會做符合公共利益之事(《論李維》,I.3);缺乏自我領導的能力,在有領袖的領導下才能展示出力量(《論李維》,I.44);擁有野心,甚至出於必然要去侵犯他人【11】(《論李維》,I.46);易於在安閒的環境下沈湎於奢華和惰怠(《論李維》,I.1)。【12】在這一人性圖景中,法律的強迫使得人民作出符合公共善的行為,構成了維繫共和自由的支柱。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斯金納更多地描繪了靜態的結構,即在常規狀態下平民接受法律的強迫,做出符合公共善的行為。但是同時我們也應當注意到,這一靜態的結構並沒有包含馬基雅維利論述中超常規手段的內容。筆者提出的質疑有如下幾點:(1)在邏輯的角度上看,法律恰恰產生於平民與貴族的對抗,如果堅持共和自由依賴於法律的強迫,那麼動亂之時勢處於缺少法律的情景。換言之,恰恰是缺乏法律強迫的平民在與貴族的對抗中創造出了強迫自身的法律,那麼使得平民能夠創造良善法律的力量無法存在於法律之中。【13】(2)在經驗的角度上看,法律也有其不足:其一,法律並不統攝政治生活的全部:在馬基雅維利引述的羅馬諸多危機中,危機的化解往往通過貴族與平民的「對話」完成,而並非直接將法律運用於具體情境作出判決;其二,法律對公民的限制並不充分:馬基雅維利指出在共和晚期,不斷更新的法律已經不足以讓人們向善(《論李維》,I.18),法律如果沒有政體【14】和習俗的配合無法單獨發生作用,事實上馬基雅維利的討論已經指向了法律之外的因素;波考克高度關注這一問題,故而他區分了德行與德性,將羅慕路斯-努馬建立的軍事-宗教秩序視為公民德性得以建立的基礎和構成要素。【15】正如波考克所說,「我們接下來必須去尋找自身並不合法,然而卻導致這一結果的行動」。【16】但是波考克將焦點放置於羅馬開端最初秩序中的力量,根據這一基礎所推論的公民德性卻又並不能完全貼合馬基雅維利的文本,對公民德性下的人性圖景作出了過於樂觀的判斷。綜上所述,波考克與斯金納對《論李維》「自由」概念的共和主義解釋中,均未足夠重視動亂——羅馬良善政治的要素,也沒有將平民和貴族在羅馬政制中的不同作用展示出來。下文將借助馬基雅維利引述的幾個事例討論這一問題。
 |
| 馬基雅維利對人民本劣的看法,構成了政治解釋上的難題 |
二、 平民與貴族的互動模式
回到馬基雅維利對平民傾向的描述,我們注意到平民既是凶悍的,卻又極易遭到奴役【17】(《論李維》,I.16)。如果我們將動亂視為羅馬良好法律和治理的源泉,那麼平民上述的兩種傾向可能在動亂中造成嚴重的危險:一方面,平民在反抗貴族時,表現出的凶悍性情可能導致大規模的混亂與流血,這也正是格拉古時代後羅馬趨於敗壞時所表現出的問題(《論李維》,I.4);另一方面,平民如果易被奴役,甘願於接受他人的領導,則有可能從根本上消除鬥爭和動亂存在的基礎。換言之,馬基雅維利理想的共和自由要求平民參與政治事務,維持其自主性(無論其目的在於共和自由的維持,還是擴張以實現共和國的榮耀),則一方面要調動起平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慾望,另一方面又要將平民的力量限制在可控制的範圍內。平民凶悍而又易於接受奴役,故而不能僅僅寄希望於平民的性情;同時必須注意到我們的討論仍處於法律之外的語境之中,在邏輯上也不能完全寄希望於過往法律對平民性情的塑造。因而,我們必須尋找新的要素,以完成上述任務。【18】
在馬基雅維利關於動亂討論的核心章節中,馬基雅維利給出了一種可能性:
享有自由的民眾,其慾望鮮有危害自由者,因為這種慾望或是生於受人欺凌,或是來自於擔心自己受到壓迫。倘若他們持有謬見,仍有公民大會作為補救,那裡會有賢達出面,雄辯地證明他們如何陷入了自欺;正如圖利所言,民雖無知,若有值得信賴者告以實情,他們既有能力辨明真相,也易於服從。(《論李維》,I.4)看上去馬基雅維利「輕而易舉」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給出了法律之外的要素:平民辨明真相的能力。然而這是一段頗引人費解的論述,特別是當我們將這一段論述與馬基雅維利對平民本性的論斷結合起來。一方面馬基雅維利認為人民容易受欺騙,容易被野心和利益蒙蔽,同時難以被說服(《論李維》,I.11,I.53);另一方面馬基雅維利卻又辯護稱人民「有能力辨明真相」,能夠接受真正有利於自己和城邦的意見。支持後者的論述在全書也多次出現:馬基雅維利認為平民不會在具體的事情上受騙(《論李維》,I.47),擁有對話的可能(《論李維》I.4,I.58,III.34),在法律的規範下平民擁有政治審慎、穩定的品性以及良好的判斷力,甚至比君主更加明智(《論李維》,I.58)。我們很難想象基於相同的人性圖景,馬基雅維利會堅持截然相反的可能性。更為吊詭的是,雖然馬基雅維利揭示了人們辨明真相的可能性,但是在《論李維》引述的羅馬史實中鮮有通過公開的交流達成對於最符合公共善方案的選擇,我們看到的更多是貴族借助欺騙、強迫等等手段使平民作出符合公共善的決定。我們不妨先擱置這一對矛盾,討論《論李維》引述的羅馬史實中貴族與平民如何在動亂中互動。【19】
 |
| 辨明真相的能力,這是一段令人費解的論述 |
(一) 說服
馬基雅維利所引用的平民接受說服的事例並不多,斯普利烏斯的案例勉強可以作為參考:斯普利烏斯·卡修斯力圖通過給平民中那種恩惠,將平民爭取到自己身邊,以取得絕對權力,這一野心被元老院識破,引起了猜忌,最終平民拒絕了斯普利烏斯·卡修斯的提議,認為這是要拿他們的自由做交易(《論李維》,III.8)。在這一案例中,元老院揭露了斯普利烏斯恩惠背後的真相,也得到了平民的認同,未敗壞的羅馬平民與貴族協力粉碎了破壞自由政制的企圖。馬基雅維利承認擁有政治審慎的精英在得到平民信任時,可以說服平民以力輓狂瀾(《論李維》,I.53),然而這並非當然的情況。正是在同一章節,馬基雅維利舉出大量事例論述當信任缺乏時,城邦面臨的災禍。【20】這仍然是前文所述矛盾的延續,暫且存而不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馬基雅維利很少論及平民能夠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認識政治事務的真相,往往需要精英在集會中將真相向平民告知(《論李維》,I.4,I.53,III.34),平民更多呈現為等待被說服的被動形象。
(二) 強迫
精英強迫平民的事例也並不多見,筆者認為強迫的方式往往借助宗教的權威進行。羅馬的公民宗教在馬基雅維利的引述中具有高度的工具性,馬基雅維利並沒有過多討論公民宗教對平民道德水平或性情改造的作用。西庇歐手拿利刃,要求平民發誓不放棄家園;托誇圖斯威脅護民官龐波尼烏斯,如果不發誓撤回對父親的指控就殺死他(《論李維》I.11),這兩個事例令人懷疑,究竟是西庇歐和托誇圖斯的武力威脅,還是公民宗教發揮更大的作用。毋寧說西庇歐和托誇圖斯使用強迫手段威脅平民,而發誓所帶來的對神懲罰的恐懼保證了他們的威脅能長久發揮作用;西庇歐和托誇圖斯扮演了主導的角色,而公民宗教成為了西庇歐和托誇圖斯的工具。【21】在平民與貴族的動亂中,貴族以宗教為藉口脅迫平民放棄選舉平民執政官(《論李維》,I.13)。在對外戰爭方面,甚至將領可以依據戰局情況解釋預兆(《論李維》,I.14),只要讓士兵相信神與己方站在一起(《論李維》,III.33)。綜上,依據馬基雅維利的論述,宗教成為了精英強迫平民作出符合公共利益行為的工具,「精明(政治審慎)的人知道,很多好事情,單憑它們自身明顯的理由,尚不足以服人。所以,有心消除這種困難的聰明人,便會求助於神明」(《論李維》,I.11)。宗教是解決平民易受欺騙而又無法被說服的工具,避免了平民的肆意招致自我毀滅;然而同時必須注意,在馬基雅維利引述案例中,往往宗教自身無法發揮作用,需要有精英將宗教的武器握在手中。
(三) 收買與賄賂
在危機發生之時,羅馬貴族有時會通過向平民輸送利益同平民妥協,以實現貴族制定的政策。驕傲者塔克文在被驅逐後,元老院貴族擔心羅馬的平民投降,為了贏得平民的信任,免除了鹽稅和一切捐輸(《論李維》,I.32);在格拉古兄弟上台前,土地法問題始終是羅馬的隱患,貴族「以耐心和勤勉來緩和這一問題……有時他們接受其中的一部分內容,或是向有待分配的地區送去一群移民」(《論李維》,I.37)。羅馬早期公民以個人的財力從軍,無法圍城持久作戰,在必然性驅使下為平民發放軍餉,而事實上這只會讓平民的負擔有增無減,平民卻興高采烈【22】(《論李維》,I.51)。另外收買不限於平民全體:當護民官的野心成為羅馬政制的危險因素時,貴族有時會收買平民中的一些人,指派他們去對抗那些忤逆元老院意志的人,「使羅馬得救」(《論李維》,I.11)。綜上所述,貴族利用了平民性情中的弱點和其所控制的政治經濟資源,在發生危機時維護了自身以及共和國的利益,也同時維護了羅馬政制的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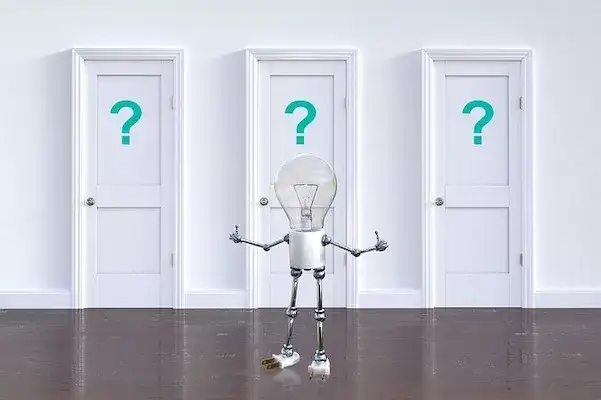 |
| 相信平民的眼睛,相信平民的眼睛是受元老貴族所影響的 |
(四) 欺騙
前文已經討論了對外戰爭中,將領根據戰局情況解釋占卜,事實上通過欺騙士兵的方式維護士兵的士氣,確保戰爭的勝利(《論李維》,I.14)。在此,筆者將通過一個具體事件,討論貴族的欺騙手段,以及平民辨明真相的能力。《論李維》I.47是討論平民判斷能力極為關鍵的章節,馬基雅維利認為平民會被大道理所騙,卻不會在具體事務上受騙:平民希望選舉產生平民執政官,元老院採取了折中的方案,設置四位具有執政官權力的護民官;然而平民雖然原本希望平民佔據更多官職,但是任命的護民官卻都是貴族。因而,在具體的比較面前(特別是事關榮譽和官職的分配),平民能夠作出符合實情的判斷,將官職分配給更好的人。這是支持平民能夠辨明真相的有力例證。
然而馬基雅維利話鋒一轉,在《論李維》I.48繼續討論這一問題。他指出,事實上貴族在選舉的過程中並非無所作為,而以其政治手腕左右了選舉結果。貴族為了避免平民出任職權同執政官相當的護民官,會採取兩種欺騙手段:要麼讓羅馬最受敬重的人謀求,要麼讓卑鄙下賤的平民參選。在這兩種情況中,平民都不會將職位分配給平民,這達成了貴族的目的。馬基雅維利稱,「這也符合上述論點,即人民即使會被大道理所騙,也不會在具體事務上自欺。」(《論李維》,I.48)
兩個章節連綴在一起構成了極為鮮明的諷刺效果:我們本以為平民可以作出獨立的判斷,認識政治事務中的真相;然而緊接著馬基雅維利便暗示,平民符合真相的獨立判斷有可能是在貴族的欺騙之下作出的。於是我們又回到了最開始的問題:究竟如何理解平民辨明真相的能力?
「真相」這一平淡無奇的概念,在馬基雅維利的使用中顯得頗為曖昧,我們不妨分殊其含義的幾種可能:(1)基於既有的、表面的信息作出符合實際的判斷;(2)透視到表面信息背後,作出使平民利益短期內最大化的判斷;(3)透視到表面信息背後,作出符合公共善要求的判斷。我們注意到,平民不會在具體事務上受騙,保證了能夠在(1)的意義上辨明真相;然而在貴族的安排與欺騙下,平民事實上並沒有在(2)的意義上辨明真相【23】(即使平民可能認為自己作出了符合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判斷);但是吊詭之處恰恰在於,雖然平民沒有在(2)的意義上辨明真相,卻在貴族的欺騙之下在(3)的意義上辨明真相。【24】簡而言之,平民辨明真相所依據的情境與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貴族建構產生的;其判斷得到的也並非赤裸的真相,而是在貴族的「引導」下得到的真相。因而,在護民官選舉這一案例中,同時可以辯護平民辨明真相的能力得到展現,以及貴族欺騙的政治手腕得到應用。「真相」概念背後,事實上是平民與貴族的鬥爭和妥協。
我們現在可以嘗試解決「說服」問題遺留的困難。馬基雅維利始終保留了平民被說服的可能性,但是前文已經提及,平民更多呈現為等待被精英說服的被動形象。退一步講,我們完全可以承認平民被說服的能力,在羅馬真實的歷史中——而非經過馬基雅維利有意識的選擇——或許在常規狀態中都能以和平的說服方式緩和動亂;但是更嚴重的危機恰恰顯現在平民受到蒙蔽而說服失效之時,這些危機時刻更深刻地揭示了羅馬政制的真實面貌。無論是說服,還是道德上存疑的強迫、收買、欺騙手段,我們都可以從中發現相同的結構:在貴族與平民的對抗中,貴族憑借其政治審慎,運用各種政治手腕駕馭了平民。平民和貴族爭奪權力,雙方都試圖壓倒對方(卻未曾成功),在鬥爭中保持了自身的自主性;平民如若聚集起來則力量強大,但在缺乏領導時卻鬆散無力,易被眼前利益和野心吸引而受蒙蔽,然而同時其性情傾向的弱點也給貴族駕馭平民提供了可能;相較而言,貴族很少動用強制性力量壓制平民(除非以宗教為中介),卻富有政治審慎,能夠抵擋平民的衝擊,並駕馭平民作出符合公共善的行動。馬基雅維利看到了平民是羅馬擴張的力量源泉,但是這一力量卻頗為盲目,甚至有在動亂中毀滅城邦的可能性;貴族無法將平民的力量消滅,卻能夠運用手段將平民的力量馴化。在這一結構中,我們甚至可以宣稱,城邦中的精英以自由而非奴役的方式扮演了「新君主」的角色。故而筆者認為,馬基雅維利贊揚的羅馬政制便是在平民和貴族巧妙的平衡中,建立起良善的法律,維持自由;相反,自由的覆滅(敗壞)不僅僅如波考克所稱是「質料」發生了變化,【25】同時是這一結構的毀滅。
⋯⋯待續⋯⋯
注釋
- 筆者無法對「敗壞」、「自由」概念作出精准的定義或概括性描述,於此試選擇其中最重要的內涵加以澄清。馬基雅維利使用「自由」概念並未區分內部自由(公民自由)與外部自由(共和國自由),在本文的使用中,除特別注明外,「自由」均指涉內部自由,特別強調其政治自主性,表現為平民與貴族在對抗中對政治事務的參與;其相對的概念即「奴役」,即絕對權力的出現破壞了平民與貴族的對抗、破壞了公民對政治的參與,後文將對這一問題展開論述。相應的,「敗壞」包括了經濟、政治與道德自主性的喪失,最終接受奴役,參考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12.需要指出的是,筆者對「自由」與「敗壞」概念的使用無法窮盡馬基雅維利的全部內涵,對概念內涵的選擇性澄清原因有二:其一,所選擇的內涵與本文討論的問題直接相關;其二,為保證概念使用的一致與明晰。
-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p.202.
- Ibid., p.184.
- Ibid., p.208.
- Ibid., p.208.
- Ibid., p.208.
- 馬基雅維利對平民的特性作了若干全稱的觀察判斷,試列舉其中最重要的判斷:「此事證實了以上所言:不出於萬不得已(即必然性),人無行善之理,若能左右逢源,人必放浪形骸,世道遂倏然大亂。」(《論李維》,I.3)「他精明而高尚,當然不會把自己掌握的權力留給別人,蓋人皆趨惡易而向善難,他善加運用的權力,他的繼任卻能用來滿足自己的野心。」(《論李維》,I.9)「眾人雖然意見各異,不知制度之益,故而不善治理」(《論李維》I.9)「的確,我還從未見過,給人民創立不同尋常的法律的人,不借助於神明,因為不然的話,他們是不會接受這種法律的。精明(即政治審慎)的人知道,很多好事情,單憑它們自身明顯的理由,尚不足以服人。」(《論李維》,I.11)「因為人們的通病是,他對表象的需要不亞於實相」(《論李維》,I.25)「因為人的自然是有野心且多疑的,並且不知道如何為他得到的好運設置界限」(《論李維》,I.29)「人民因為受偽善的表象所欺而自取滅亡……如果命運沒有讓人民信任一個人,就像過去人們因為被某人某事所騙而時常發生的情況那樣,則災禍勢所難免。」(《論李維》,I.53)「擺在人民面前的事情,如果看上去像是收益,即使背後隱藏著損失;所採取的政策,如果看上去大義凜然,即使共和國的覆滅潛藏於其中,那也不難讓民眾相信它。」(《論李維》,I.53)以上譯文參考馬基雅維利著《論李維》,馮克利譯,世紀出版集團,2005。英譯本參考Discourses on Livy, Machiavelli, Tr. by Harvey C. Mansfiel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後文引述《論李維》不再單獨注出。
- 在本文中,不加區分地使用「人民」時指人的總體,即平民與元老院貴族的總和,馬基雅維利的「人民(popolo)」概念與筆者的用法並不相同,popolo仍保留了平民的含義;在後文中,除平民、貴族之外,筆者還會引入「精英」這一概念,指具備政治審慎,並能在危機中左右局勢,維護共和政制,執行處決的關鍵人物,如布魯圖斯、托誇圖斯、西庇歐等人。精英可以約等於元老院貴族,但二者不完全相同:一方面,元老院貴族有時會做出毀滅共和的舉措,如十人團的形成(《論李維》,I.40);另一方面,平民護民官也在部分場合發揮決定性作用。需要澄清的是,並不能認為元老院貴族能始終將公共利益放在私人利益之前(即便在未敗壞的條件下),馬基雅維利明確提到貴族整體的野心和自私,如貴族在驅逐驕傲者塔克文時的偽善和驅逐驕傲者塔克文後的野心(《論李維》I.3),以及貴族在十人團建立時的態度(《論李維》,I.40);然而又不可否認的是,貴族往往是羅馬最傑出的公民(《論李維》,I.47),在部分危機時的舉措「在他們看來,是在維護公益」(《論李維》,I.37),事實上也確實做出了維護公共善的行為。綜上,貴族的形象同樣極為複雜,有關貴族的討論將在後文進一步展開。
- Quentin Skinner, Machiavelli on Virtù and the Maintenance of Liberty, in Visions of Politics, Volume II, Renaissance Virtu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78.
- Ibid., p.177.
- 以上僅僅討論平民的傾向。貴族同樣存在嚴重的野心,企圖壓制平民;而最好的公民甚至會在野心的驅使下敗壞成為最壞的公民(《論李維》,I.42)。筆者認為,對平民傾向的討論是更為重要的,原因在於平民是羅馬擴張的力量源泉(對比威尼斯、斯巴達,《論李維》,I.5),然而平民自身又是近乎於盲目而凶猛的力量,羅馬必須通過超常規或常規手段將平民的力量加以限制和導引,使之適合於共和政制與軍事擴張的需要,這成為《論李維》的重要主題。對於貴族而言,防範野心更為關鍵,平民護民官等制度的建立旨在規避野心膨脹破壞共和自由的可能。
- Skinner, Machiavelli on Virtù and the Maintenance of Liberty, pp.160-176;參考吳增定:《馬基雅維里論人民》,載於《哲學動態》2016年第6期,第47頁至第60頁。
- 固然我們可以辯護稱,在過往法律的強迫下,平民與貴族在對抗中創造出了新的良善法律;但是邏輯地看,這樣的解釋勢必造成無限後退,追溯到超出法律的力量。我們可以進一步為斯金納的立場辯護,即無限追溯的結果仍然是立法的行動,即羅慕路斯-努馬建立的軍事-宗教秩序基礎。然而這一辯護也存在困難:其一,固然馬基雅維利承認羅慕路斯建立的君主政制蘊含著通向自由政制的可能(《論李維》,I.9),但是這也僅僅是可能性而非必然性,筆者試圖提出的辯護表達了如下的傾向:即羅馬後世的自由政制已經被羅慕路斯-努馬的立法預先決定。而馬基雅維利明確稱,羅馬是經歷了無數變故和鬥爭、完善的過程後才建立起了自由政制,這一解釋忽視了歷史事實中平民與貴族間對抗的過程(《論李維》,I.2)。其二,這一立場事實上已經非常接近於波考克的立場,下文將繼續討論。
- 秩序(ordini)這一概念在《論李維》中也包含多重含義。在一般意義指涉各種秩序,如軍事秩序;而同時還有特殊用法,即「政府的秩序」「國家的秩序」,即平民、元老院、護民官、執政官的權威,產生官吏的方法,立法的方式(《論李維》,I.18),這一用法更接近於古典的「政體(politeia)」概念,較之前者更加根本。在後者用法中筆者將直接使用「政體」概念,在前者用法中使用「秩序」概念。
-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p.194.
- Ibid., p.194.
- 值得注意的是,馬基雅維利關於平民的傾向,給出了近乎是截然相反的兩組敘述。我們需要對兩種傾向加以區分:在共和國維持了平民與貴族良性互動的關係下,平民擁有政治自主性,此時平民處於「自由」的狀況下,卻始終保存著濫用自由、壓倒貴族的傾向,表現為平民的凶悍;然而當平民與貴族的良性互動被打破,平民訴諸於私人性的解決,即訴諸於僭主時,平民接受了僭主的奴役,此時平民傾向表現為易於接受奴役。兩者並存於平民的傾向之中,然而其表現應視具體的政治、經濟環境而定。
- 需要澄清的是,筆者的討論將從平民傾向的一個方面出發,即平民的凶悍。筆者揣測,馬基雅維利之所以未對內部自由與外部自由進行區分,原因在於他認為二者同源,均要求人民保護自主性,拒絕接受奴役。我們注意到,馬基雅維利引入「自由」這一概念時在對城邦進行類型學的劃分,城市要麼由自由人建立,要麼由依賴於他人的人建立,甚至母邦殖民建立的共和國也被歸為非自由,佛羅倫薩共和國便歸於此類,此處使用外部自由的含義。在隨後的討論中,內部自由含義的使用逐漸增多。依照馬基雅維利的區分,自由應是內部自由與外部自由的全部保存,其中心意義在於城邦居民對他人不存有依賴。只有嚴格意義的共和國才能滿足自由的要求,佛羅倫薩便處於曖昧不清的地位(《論李維》,I.1)。因而共和政制在概念上便與政治參與的要求、保證公民政治自主性的性情(即傾向於自由,卻又容易濫用而壓制他人)相關,而與接受奴役的傾向相悖(相應的,君主政制或母邦建立的殖民地則與易於接受奴役的傾向相聯繫)。同時,在馬基雅維利看來,共和政制下習慣於自由生活的平民會從尋求不恐懼發展成為要讓他人恐懼,即從保護既有政治自主性發展出壓制貴族的傾向(《論李維》,I.43)。筆者會從這一傾向出發,給出走向奴役,喪失自主性的解釋。
- 筆者將在下文列舉「說服」、「強迫」、「收買與賄賂」、「欺騙」四種互動模式。「說服」意指精英將合乎公共善的方案告知平民,平民因對公共善的認知而接受該方案;「強迫」意指精英使用武力手段逼迫平民作出合乎公共善的決斷;「收買與賄賂」指貴族借助掌握的經濟、政治資源,向平民輸送利益使其支持某一方案;「欺騙」指貴族運用政治手腕向平民隱瞞部分信息,或提供虛假信息,使平民在片面或錯誤的信息基礎上作出決斷。
- 馬基雅維利引述法比烏斯、佩努拉、西庇歐、尼西阿斯、梅塞爾·厄爾科勒·本蒂沃廖的例子討論這一問題。法比烏斯、西庇歐的例子尤為關鍵,因為此時羅馬仍未敗壞,貴族仍然不得不順從平民的性情,無法糾正平民所受的欺騙,甚至馬基雅維利宣稱「欲使共和國覆滅,最為便捷的辦法,就是讓人民投身於大事業;凡是吹捧他們的人,他們總是笑納不爽;即使有人反對也無濟於事」(《論李維》,I.54)。在文本的編排上,I.54與I.58僅隔三章,立論卻大相徑庭,前者嘲諷平民,後者卻贊頌平民,不免讓人對馬基雅維利的態度頗為困惑。
- 馬基雅維利所引述的大量事例都與強迫下的發誓相關,類似的還有:盧伯烏斯逼迫平民發誓遵從執政官,暴力收復神廟,而即便護民官挑戰宗教的作用也無濟於事(《論李維》,I.13);薩莫奈人逼迫士兵在手持利刃的百人隊隊長中間發誓不臨陣脫逃,不敢發誓者當即斬殺(《論李維》,I.15)。
- 這同時是平民無法被說服的例證。護民官告知平民事情的真相,籌措軍餉只會讓稅負增加,但是平民已經被眼前的利益蒙蔽(《論李維》,I.51)。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到貴族的政治審慎,一方面實現了共和國擴張的目標,實現了公共善;另一方面滿足了自身的利益,給自己加設最多最重的稅負,同時也獲得最多的支付。因而我們同時看到貴族自私的傾向,同時又看到貴族對公共利益的操持,其形象的複雜性使我們無法簡單地評判貴族是否做到了將公共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前。事實上馬基雅維利所引述的羅馬貴族往往利用政治手腕維持羅馬政制中平民與貴族微妙的平衡。
- 依據馬基雅維利的論述,以及文本的結構安排,馬基雅維利留下了一種可能性:原則上平民本可以將職位授予最傑出的平民,但是這一可能性被貴族借助其欺騙手段排除了。
- 馬基雅維利對共和政制的設想要求平民與貴族對抗,而又避免其中一方的覆滅,雙方在良性的互動中實現良善治理。若平民執政官產生,則有進一步平民壓倒貴族的可能性;然而筆者將會指出,依據馬基雅維利的引述,羅馬共和政制的運作依賴於貴族對平民的領導,貴族操持的政治平衡符合羅馬的公共善。前文已經指出,貴族的形象非常複雜,令貴族出任執政官以及同職權同執政官相當的護民官,既維護了自身的利益,抵抗平民的野心,同時也維繫著共和政制的良性運轉。
-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p.207.

留言
張貼留言